阅读:0
听报道
老子的《道德经》开篇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多少年来,诸多注家都大致解为“‘道’,说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的‘道’”(任继愈《老子绎读》译文,下文所引《老子》原文亦依据该书)。但最近我在报上看到赵汀阳先生的一篇文章《继续生长,经典才能不死》(《中华读书报》2015年1月21日第9版),文中对此句提出了一种全然不同于以往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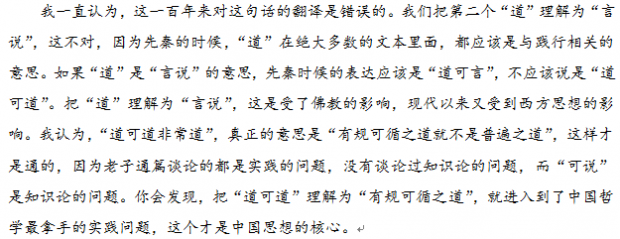
赵先生的意思似可归结为三点:(1)这一百年来人们把“道可道”的后一个“道”译为“言说”是错误的,“道可道”应解为“有规可循之道”。(2)在先秦时,“道”在绝大多数文本中都表示与践行相关之义;把“道”理解为“言说”是受了佛教的影响,后来又受到西方的影响。(3)“可说”是知识论的问题,故与通篇谈论实践问题的《老子》不搭界,而只有按照赵的理解,才会进入到中国哲学最拿手的实践问题,而这正是中国思想的核心。
赵汀阳的说法在《老子》(也即《道德经》)研究领域也许可称得上“石破天惊”之言,我乍看到此文也觉颇有创意,还用手机照下来发给朋友参考。后来静下心来细想,又产生了不少疑问。这些天来,为了求证赵的说法又翻了几本古书,这些工作和思考使我得出了与最初看到此文时完全不同的结论,下面就写出来与赵汀阳先生商榷,并就教于方家。
一
当赵汀阳说“这一百年来对这句话的翻译是错误的”之时,他似乎忘记了一个事实:对“道可道”的解释并不止于这一百年,早在两千多年前,法家的著名理论家韩非便在其名篇《解老》中对这句话作了最早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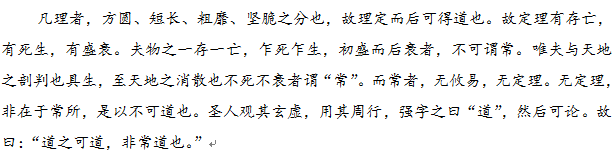
在韩非看来,“理就是万物的方圆、短长、粗细、坚脆的区别,因此理确定以后事物才可能得到说明。所以确定的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万物有存有亡,忽生忽死,先盛而后衰的,不能叫做常(永恒)。只有那种与天地的开辟一起产生,到天地消散仍然不死不衰的才叫做‘常’(永恒)。所谓常(永恒),是说没有变化,没有定理。没有定理,不处在固定的某一点上,因此无法说明。圣人观察到‘常’的玄虚,依据它普遍运行的法则,勉强给它起个名字叫做‘道’,然后才可以论说。所以《老子》上说:‘道如能用话说得出来的,就不是永恒的道了。’”(韩非原文和译文均源自《韩非子》校注组编写,周勋初修订的《韩非子校注》(修订本),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以下所引《韩非子》文句亦出自该书。)
对这段译文的“信”和“达”,人们当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赵先生也可以说,这段译文的最后一句话仍然沿袭了这一百年来的错误。好在这是一段话,而不像《老子》中仅为一句话,我们自可从韩子的整段话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从前往后看,“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此处的“道”,似乎只能理解为“言说”(而就在此段后第五段,在同一语境下韩子又有“理定而物易割也”之说,这里的“割”是“分析”的意思,也是“言说”,当可与此“道”参照理解);如果你硬说它是“遵循”之意,那么这些万物的“方圆、短长、粗细、坚脆的区别”确定之后,它得以“遵循”的又是什么?这么理解与上下文接得上吗?请注意,韩子在此并不涉及万物是否“有规可循”的问题,他关心的是“理”的短暂与恒久的问题——“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常’。”译文把这个“常”译为“永恒”我以为是贴切的。而此无变化无常理且无固定所在的“常”也因此而无法用言语来描述——“而常者,无攸易,无定理。无定理,非在于常所,是以不可道也。”请问赵汀阳先生,此处“是以不可道也”之“道”,如果不是“言说”,又是什么?如果说它是“遵循”,那么便是说韩子在此阐释的“常”是“不可遵循的”。但这种理解恐怕韩子难以苟同,因为他下面有话:“圣人观其玄虚,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然后可论。”即韩子把这里所说的“常”命名为“道”,而就在这篇《解老》中,在此段前边隔一段,韩子便有对“道”的明确阐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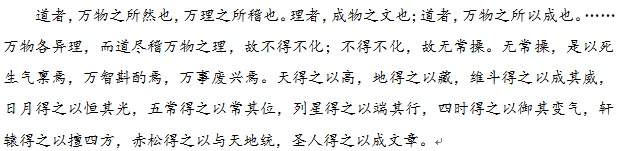
(末句“文章”在周书中注为“文采,这里指礼乐刑政等文物制度”。)由此可知,在韩子心中,“道”不仅可被大自然得之,也可被圣人得之,由此才会有作为盛世保证的“文章”。在这段前边,他曾指出“有道之君,外无怨仇于邻敌,而内有德泽于人民”;“人君无道,则内暴虐其民,而外侵其邻国”。如果韩子认为道“不可遵循”,那么,他所说的“得之”,他所说的“有道”“无道”,又当怎讲?而在前边,在解释《老子》五十八章时,韩子更是明确提出:“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并说:“众人之轻弃道理而易妄举动者,不知其祸福之深大而道阔远若是也”。“缘道理以从事”难道有一丝一毫“道不可遵循”的意思吗?因此,着眼于全篇,“是以不可道也”之“道”,只能理解为“言说”。但此不可道也的“常”,为了便于阐释,于是老子便“ 强字之曰‘道’,然后可论”。注意,此处的“可论”与前边的“不可道”适成对照,韩子似乎预测到两千年后可能有人会对作为“言说”的“道”作出不同的解释,预先在此加以说明一下,接着便引出了“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至此,韩非对老子这句名言的解释似乎是明明白白了。
看来,“道可道,非常道”,不仅“这一百年来对这句话的翻译是错误的”,而且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中国第一位解释老子的韩非就因为不能很好地理解先秦语言而把老子的本意领会错了!
二
赵汀阳说,在先秦时,“道”在绝大多数文本中都表示与践行相关之义;把“道”理解为“言说”是受了佛教的影响,后来又受到西方的影响。为了验证赵的说法,我特意翻了翻几本先秦的典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在先秦的语言中,表示“言说”的词不少,如曰(前面可加上各种不同的修饰词作“曰”的状语,或与“言”“谓”“告”等词构成复合词,如故曰、对曰、命曰、告曰、誓曰、辞曰、皆曰、谏曰、怒曰、诗曰、书曰、再拜曰等,以及言曰、号之曰、谓之曰、告之曰,等等)、云、言、语、谓、名等。除了表示“说”的“曰”之外,可能“言”字用得最多,它不仅有“说”的意思,还有“话”“语言”“对……说”等意思,表示这类意思时,“言”以及与之相似的“语”“谓”“名”等均不能用“曰”来代替。例如:
1.武子曰:吾言于君,君弗听也。(《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2.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3.晏子谓桓子:必致诸公!(《左传•昭公十年》)
4.言。故言也者,诸口能之,出名者也。名若画虎也。言,谓也。言由名致也。(《墨子•经说上》)
5.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庄子•秋水》)
6.圣人之爱人也,人与之名,不告则不知其爱人也。(《庄子•则阳》)
7.四时殊气,天不赐,故岁成;五官殊职,君不私,故国治;文武殊能,大人不赐,故德备;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则阳》)
注意,4,6,7中的“名”分别表示“名词,语词”“称说,命名”“名称”之意,而“道不私,故无名”中的“道”可对应于“道可道”中的第一个“道”,其中的“名”则对应于“道可道”中的第二个“道”。
“道”在先秦典籍中有多种含义,例如:
1.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
2.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
3.今以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以相群居,以相持养,以相藩饰,以相安固邪?(《荀子•荣辱》)
4.传曰:从道不从君。(《荀子•臣道》)
这些“道”有“规律”“法则”“治国之法”或“治理之途”“(正确的)原则”等意思,但均没有《老子》之“道”(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的内涵丰富广泛。
5.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此“道”意为治理。)(《论语•学而》)
6.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两个“道”都指道义、道德。)(《孟子•公孙丑下》)
7.子蒲曰:吾未知吴道。(此“道”意为方法。)(《左传•定公五年》)
8.道者,何也?曰:君子之所道也。(第二个“道”是“遵行的原则”。)(《荀子•君道》)
9.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如保赤子。(第一个“道”是“遵行”,第二个“道”是“引导”。)(《荀子•议兵》)
10.及吴师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此“道”亦为“引导”。)(《左传•哀公八年》)
11.刘子从尹道伐尹。(此“道”为“道路”)(《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12.三月,吴伐我,子洩率,故道险,从武城。(“故道险”为“故意从险道行军”。) (《左传•哀公八年》)
13.叔向曰:单子其将死乎!朝有著定,会有表;衣有禬,带有结。会朝之言必闻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视不过结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两个“道”都为“治”,引申义为“端正”。)(《左传•昭公十一年》)
“道”在先秦典籍中的几种常见用法和语义已如上述。问题在于: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道”在先秦典籍到底有没有表示“言说”的用法?其实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证问题——某大学者早已有言在先:说有易,说无难。赵汀阳先生敢于对先秦之“道”表“言说”说无,足见其胆识过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先秦典籍竟然不领佛教的情,硬是“违规”地一再用“道”(见下例中各黑体字之“道”)来表示“言说”之意:
1.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诗经•鄘风•墙有茨》)
2.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3. “如切如磋”者,道学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大学》)
4.《皇矣》道之曰:帝谓文王,予怀明德,……顺帝之则。(《墨子•天志中》)
5.非独子墨子以天之志为法也,于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然:“帝谓文王,予怀明德,……顺帝之则。(《墨子•天志下》)
6.《太誓》之道之曰:纣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墨子•天志中》)
7.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
8.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孟子•滕文公上》)
9.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庄子•齐物论》)
10.(孔子)曰:“丘也闻不言之言矣,未之尝言,于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孙叔敖甘寝秉羽而郢人投兵。丘愿有喙三尺!”彼之谓不道之道,此之谓不言之辩,故德总乎道之所一。(《庄子•徐无鬼》)
11.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其明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庄子•天下》)
12.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庄子•天下》)
13.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荀子•儒效》)
14.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举,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君子之谓吉,小人之谓凶。故长短、小大、善恶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荀子•非相》)
15.孙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荀子•议兵》)
16.孙卿子曰:凡在大王,将率末事也。臣请遂道王者诸侯强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势。(《荀子•议兵》)
17.请成相,道圣王,尧舜尚贤身辞让。(《荀子•成相》)
18.孔子对曰:所谓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邑邑……(《荀子•哀公》)
19.今学者皆道书策之颂语,不察当世之实事,曰:上不爱民,赋敛常重,则用不足而下怨上,故天下大乱。(《韩非子•六反》)
20.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末条《史记》虽不是先秦典籍,但其成书年代亦早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学界公认的佛教开始传入东土时间)百年以上,便也顺带录以备考。)
看罢这些来自先秦典籍的例证,大概不会再有人对当时的“道”字可表示“言说”之意有什么疑问了吧?
三
赵汀阳说:老子通篇谈论的都是实践的问题,没有谈论过知识论的问题,而“可说”是知识论的问题。
在我看来,汉语中的“可说”有多种涵义,例如可叙述,可引述,可评述,可对外散布,可阐释,可论证等等,在某一语境下,它并不必然等于“可论证”或“可阐释”,而且即便它就是“可论证”或“可阐释”,也并不等于“在当下论证”或“在当下阐释”,而很有可能只是虚晃一枪,转身便“说”别的事去了。 也即当“可说”出现时,所说之事并不必然意味着已进入知识论的领域(事实上,墨子的《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大取》《小取》倒确实是进入了知识论的领域)。从上述20条例证中,不难看出这一点。
赵汀阳在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道”是“言说”的意思,先秦时候的表达应该是“道可言”,不应该说是“道可道”。赵的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事实上,当我们把“道可道,非常道”的第二个“道”理解为“言说”时,则由此句便可推出“(常)道不可道”,也即“道不可道,可道非道”,而这便是《庄子•知北游》中的一段话:“无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无始曰:有问道而应之者,不知道也。”哈,赵先生的猜想(如果“道”是“言说”的意思,先秦时候的表达应该是“道可言”)竟然是对的!也即按照赵先生的逻辑,“道”是“言说”的意思已得证(唯一的不足仅在于,此处论“道”的是庄子而不是老子)。同时考虑到庄子在前述《齐物论》中的“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考虑到《老子》第二十五章中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以及《老子》第三十二章的“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则“道可道”即“道可言”已是非常明白了。那么,老子为何不按照“先秦时候的表达”写成“道可言”呢?
《老子》的第一章前两句是这么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这两句中,第一、三个“道”与第一、三个“名”是对应的(都是表示概念的名词);如果第二个“道”是“言说” 的意思(根据本文一、二部分的解释和例证,这一点已很清楚),它与第二个表示“叫得出”(也是一种“言说”)的“名”自然对应得很完美。反之,如果如赵汀阳所说:“老子通篇谈论的都是实践的问题,没有谈论过知识论的问题,而‘可说’是知识论的问题。你会发现,把‘道可道’理解为‘有规可循之道’,就进入到了中国哲学最拿手的实践问题”,那自然是很美妙的,只是此时赵先生似乎完全忘记了下面还有一句“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似乎没有那么低能,在第一句进入了“中国哲学最拿手的实践问题”之后,随即便毫不犹豫地跳入了谈“可说”的“知识论”的陷阱——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当赵汀阳无法把“名可名”的第二个“名”从“言说”的理解中拯救出来时,这种“‘可说’是知识论的问题”与“老子通篇谈论的都是实践的问题,没有谈论过知识论的问题”便出现了无法解决的矛盾。
老子不说“道可言”而说“道可道”,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问题。作为我国先秦时代最伟大的哲学著作,《老子》又称《道德经》,既然是“经”,它就如《左传》《墨子》《韩非子》中的“经”一样,具有简洁精警的特点,不仅如此,《老子》中的语言在许多地方如同《韩非子》中那独具一格的《扬权》一样,也具有韵文的美妙风格。不论是就文章的哲学抽象的高度和所引发议论的广度及深度来说,还是就语言形式和声音的美感而言,显然,“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比“道可言,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或“道可言,非常道。名可言,非常名”要强得多。
老子作为孔子的前辈或同辈,其生活的时代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相距不远(柏拉图生于孔子去世后52年,约与墨子是同时代人)。我们不妨略微瞥一眼当时西方圣哲的哲学论辩(以下柏拉图著作译文源自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柏拉图在其名著《国家篇》(又译为《理想国》)中曾描述了哲人苏格拉底与友人们所进行的一场关于何为正义的辩论。当直率的塞拉西马柯说出“正义无非就是强者的利益”,“干坏事干得最多的人就是最快乐的人,最不愿意为非作歹的人也就是最倒霉的人”时,苏格拉底则通过论证“正义者不向他的同类而向他的异类谋求利益,不正义者既向他的同类又向他的异类谋求利益”,从而引导论敌一步步和他一起得出这样的结论:“正义是德性和智慧,不正义是邪恶和无知”。在那篇最难理解的《巴门尼德篇》中,柏拉图以少年时代的苏格拉底作为听众之一,见证了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巴门尼德那精彩绝伦的逻辑推演(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柏拉图的创作)。巴门尼德从“假如一存在”以及“假如一不存在”共提出了八个问题,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基于语词的多义性并具有高度抽象性的论辩,他的论证是从这段话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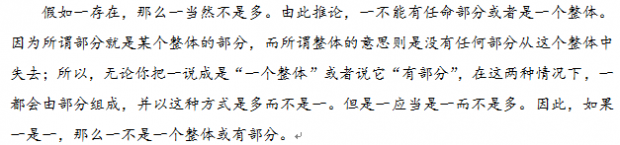
接下来,经过走迷宫似的层层逻辑推理,论者对每一个假设的命题均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真可谓“把活的说死,把死的说活”, 足以把未受过专门训练的读者逼疯。毋庸讳言,在逻辑推理方面,中国先秦哲学同古希腊哲学的确存在差距。但作为中国哲学的骄傲,《老子》首次提出了“道”的宇宙观,在对“道”的多层面多角度的阐释中展现了一种远高于
聪明干练的人生智慧,其远见明察、高妙圆融,千百年来都让人叹为观止。如果说,在这篇伟大的“五千言”中,慧黠的老子也会故意玩一点儿基于语词多义性的抽象玄妙的语言戏法,岂不是顺理成章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赵君何怪哉?窃以为,不论是否“进入到了中国哲学最拿手的实践问题”,以“道可言”来解释“道可道,非常道”,只会加深而不是歪曲人们对《老子》的认识和理解,只会提高而不是降低这位古代圣哲在当代世人心中的地位。
袁 元
二○一五年三月七日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